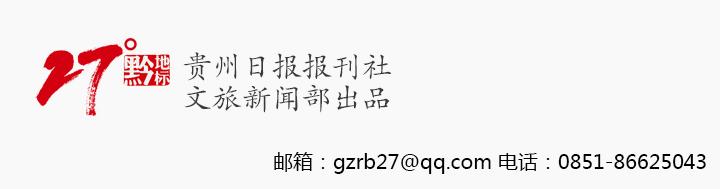
今年7月,中国作家协会公布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2025年第1期3部入选作品,来自贵州毕节的青年作家曹永最新长篇小说《穿山记》入选。
据悉,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评选结束后,一位评委在讲座上谈论《穿山记》时说:“这个故事非常难讲。这个构思,确实花费了许多心血。故事推进几十年,都没脱离主人公有限的听觉和嗅觉。”
曹永则形容《穿山记》的写作过程为“失眠之作”——这部以黔西北农民悬崖凿渠为背景,以盲人牛天光为主角的小说,讲述了贵州人在时代进程中,坚韧不拔的奋斗故事,是回应“新时代山乡巨变”这一命题的实践和回应。

进入文学:废墟里长出的花草
“文学是我这片废墟里长出的一株花草。”曹永如此定义写作的意义。
追溯写作的源头,曹永说自己的文学之路始于偶然。老家乡镇青年作家的出现和书店里随手翻开的书籍,激发了他创作的念头,点燃了这个离开校园、做事屡屡受挫的年轻人的文学野心。
“讲来荒诞,一个毫无准备的年轻人,就这样无知而冒失地闯进了文学的殿堂。”他自嘲道。
作家薛荣说,有时候,一个人的写作就像一条河流。在曹永眼中,他虽没从源头出发,但随着这条河流漂荡至今,文学不仅拓展了自己生命的长度和宽度,通过笔下的人物,还能感受不同的人生。

曹永。受访者供图
“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我,进入文学世界后,我可以随意分身,幻化成无数个我。我身无所长,觉得自己就是一片废墟。而文学创作,就是这片废墟里长生的一株花草。”
在农村长大的曹永,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,后来想去当兵被查出身患严重的脾脏疾病,在家休养了很久……康复后,他学着父辈们的模样,一年四季在土地里忙碌,播种翻土、浇水施肥,直到文学的种子彻底点燃心里的燎原。
这些在生活中历经的苦难和危机,虽未直接转化为创作素材,却锻造了曹永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。
“对写作者而言,苦难并不是必需的基础。甭管我们经受的是疾风骤雨,还是柔风细雨,所有这些经历和见闻,全都可以转化成创作的素材。”曹永认为,人在经历困境和绝望之后,思想也可能会发生变化,比如写作中断多年,再次提笔的时候,发现思考的问题和当年早已不同。

乌蒙山风光。陶泽祥 摄
“穿山”背后:在地性写作如何呈现时代叙事
此次入选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作品《穿山记》,它的诞生对曹永而言,更是一场与自我的博弈。
失眠困扰下的曹永,耗时数年才完成这部“失眠之作”。故事里,他将主人公设定为盲人牛天光,在悬崖修渠的壮举中,主角仅依靠听觉与嗅觉推进叙事。
“一个评委说这故事‘非常难讲’,但正是这种难,让我必须找到文学的突破口。”曹永说,用《穿山记》作书名,指向凿渠引水这个贯穿始终的事件,它既指地理上的穿越,也指心理上的穿越。
《穿山记》里的主人公在固定的山洞苦熬8年,终于修通渠道,跟着修渠的队伍回到久违的山寨。曹永通过残障者的感官限制,不仅完成了地理意义上的“穿山”,更隐喻了观念冲突中的精神突围——父辈与子辈从对抗到和解,最终“走向统一的路径”。

在威宁草海上飞翔的黑颈鹤。何育勇 摄
谈及小说中蕴含的传统元素和黔西北方言,是否会造成非本地读者的阅读门槛。曹永以从《毕节县志》里找到的灵感“端公复活”为例,谈到传统文化现代叙事的融合。
“我们的写作,大半部分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。问题在于,我们怎么把这些传统的东西,融合到作品之中。”他认为,传统与现代的紧密结合,不会带来阅读阻碍,反而能让地域故事拥有更广阔的共鸣。
这种平衡在《穿山记》中以先辈在绝境中创造的奇迹,成为对“山乡巨变”有力的文学化诠释。
从曾经光秃秃的威宁群山到今日绿意盎然的磅礴乌蒙,曹永笔下的乡土“痛感与温情并存”,这既是对变迁的记录,亦是对根脉的凝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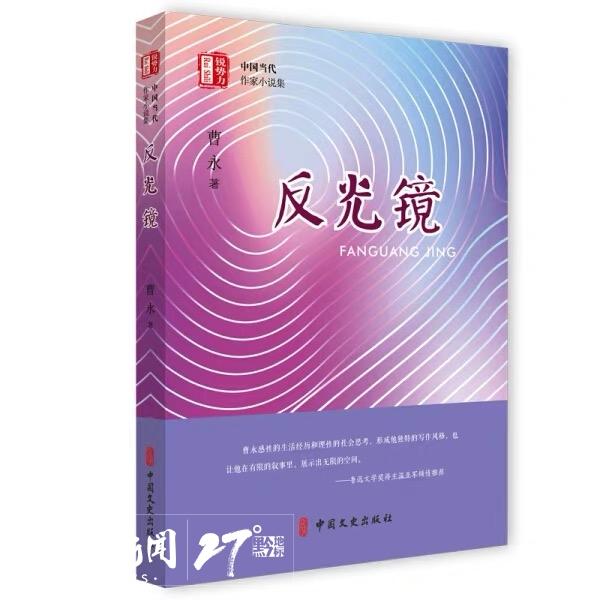
转向长篇:身体与意志的拉锯
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,曹永以中短篇小说见长。短篇小说集《反光镜》于2020年获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年度大奖;中短篇小说集《世上到处都是山》获首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短篇小说佳作奖等。
从中短篇转向长篇,《穿山记》带给曹永的最大挑战并非结构或节奏,而是“身体与意志的拉锯”。
曹永说,原计划的单线叙事,双重结构,在准备大改后打算再构思。他笑称:“作品和失眠一样,不受控地长成了现在的模样,重构之后,察觉之前的结构改变了,它们最终走向统一。”他透露,完成《穿山记》修改后,将尝试以中篇“找回手感”,再推进完成构思的几部长篇计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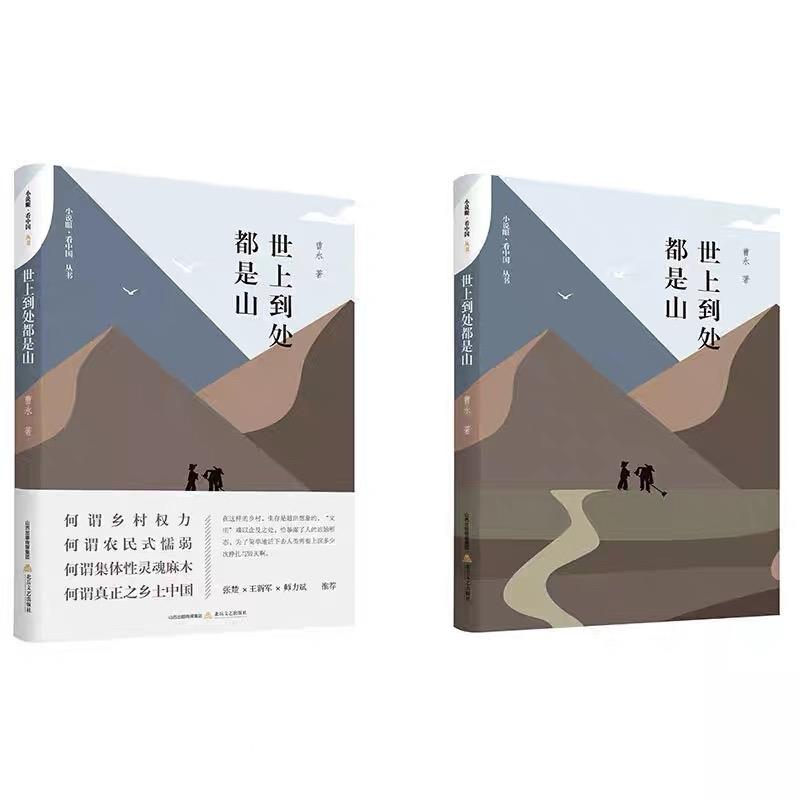
作为曹永的文学粉丝,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授、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朝认为,曹永的文字是从乌蒙山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,就像高原上的苦荞,开花的时候是苦的,果实一开始入口也是苦的,但仔细品尝之后却是回甜的。
“透过曹永的文字,我们能看到这片土地上的人身上的那股子韧劲和狠劲,他们一直追逐着生存的氧气与做人的尊严。他的作品中不仅有批判,还有满满的期许。”江西省作协副主席樊健军如是评价。
或许,《穿山记》的悬崖渠水,不仅流淌着曹永对文学近乎执拗的信仰,也是废墟上那株花草的滋养。
从乡镇青年的懵懂提笔,到今日以残障者视角叩问时代命题,曹永的创作始终与土地、与困境紧密缠绕。就像他所说的,“靠着日积月累的耐性,通过漫长的思考领悟、长期刻苦的修炼,有了感知,文学也就诞生。”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
文/陈江南
编辑/王子琪
二审/姚曼
三审/黄蔚 陈曦

